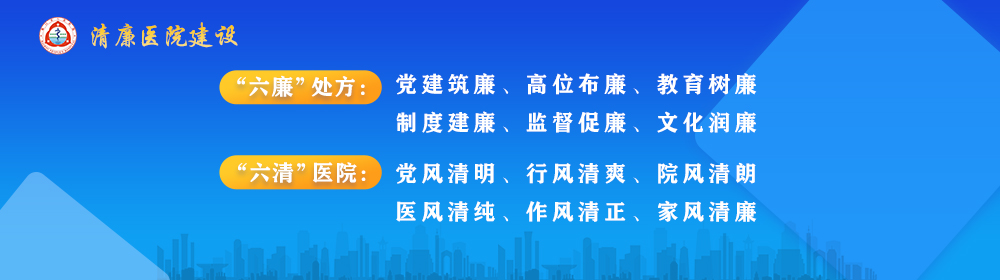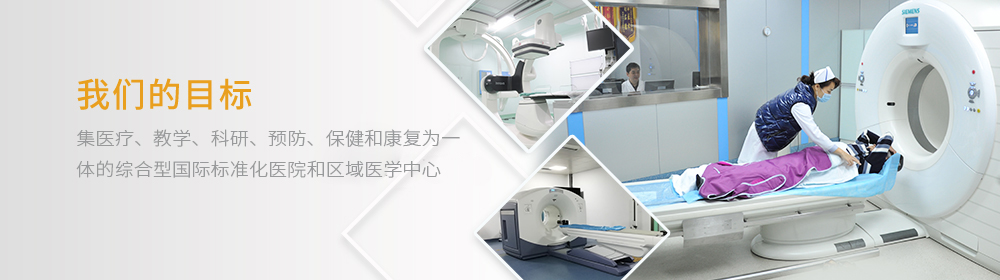我家乡位于澄迈县老城镇海边,村前是一个天然海港,名叫东水港,家乡因港得名,名叫东水港村。村子隔海对面有一条长长的沙湾,名叫“边湾”,“边湾”上有一个天然淡水池,名叫“冯公窟”。
这个淡水池为何名叫“冯公窟”?“冯公”又是何许人?
这些疑问,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,在与村中的一位长辈闲聊中才偶然得到答案。
原来,这个“冯公”不是一般的冯公,而是被海南人世代敬为神明的冼太夫人的丈夫冯宝(冯公宝)。传说当年冯公宝与冼太夫人来治理海南时,经常带兵到各地巡查,有一次路过“边湾”,当时正值盛夏,天气炎热,人马饥渴难耐,幸亏士兵在附近找到这口淡水池才化解困境。为了纪念冯公来过此地,人们便将淡水池叫做“冯公窟”,从此世代相传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,“冯公窟”还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。其周边都是茂密的树林,加上荆棘丛生,村里人都视之为畏途,只有个别胆大的人到其周边找柴火时偶尔去取淡水喝。回来后便添油加醋给小孩们描述那里是如何如何的偏僻、如何如何的吓人。当时我才八、九岁,听了大人对“冯公窟”的描述,在好奇心的驱使下,忍不住约了两个小伙伴瞒着父母,偷偷去了一回,至今情景犹记:树林中有一个水池,不大也不小,水色幽蓝,深不见底,水面长有水草,边上长有许多芦苇和野菠萝,寒凉之气逼人,周围环境寂静得令人心里发怵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有一次回老家,在与同村一老友闲聊时又提起“冯公窟”,俩人一时兴起,便叫朋友摇船送我们到边湾重找“冯公窟”。但几十年过去,那里的环境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,具体方位已记不清,加上植物茂密,找了半天,最终也没找着,只好悻悻而归,但重找“冯公窟”的念头却难释怀。
2006年,鲁能集团投巨资在老城盈滨半岛重建永庆寺,马路也修到了“边湾”,交通方便了,我与老友再次去寻找“冯公窟”。当时正好有位老乡在永庆寺附近养虾,他很熟悉“冯公窟”,主动为我们带路,不到十分钟,便找到了“冯公窟”。但重见“冯公窟”时,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,呈现在我眼前的“冯公窟”已经不是记忆中的“冯公窟”:茂盛的植物没有了,池边乱搭着简陋的养鸡场,附近养虾场的污水也直排入池,池水已变得混浊。面对着面目全非的昔日神池,我的心情格外沉重。
重新找到“冯公窟”后,每年回老家过春节,我总喜欢先绕路去看看它,担心不知那天就见不着它了。因为盈滨半岛开发正如火如荼进行,而开发总是伴随着破坏,推土机整天隆隆作响,在利益的驱使下,谁能理会一方乡愁,谁能保证“冯公窟”最终不被填埋?作为一介书生,我所能做的是,就是尽可能让多些文人墨客来参观它,了解它,好让它能留在翰海中,即使有一天它消失了,后人还可以从文字中了解它曾经的存在和风采。
有了这样的想法,再次面对“冯公窟”时,我的心情便变得轻松起来,让“冯公窟”走进文人墨客的视角最终也初步得以实现。
2015年11月25日,经我谋划,古老的“冯公窟”终于破天荒迎来了东水港子孙为它安排的一次文化盛会。当天上午,秋阳高照,惠风和畅,应东水港村《浪花吟》编委邀请,《老城春秋》主编王广元先生、责任编辑张萍女士、老城中学原校长姜维民先生以及多位文人雅士,在我的带领下兴趣勃勃地来到了“冯公窟”游览。因为周围的虾场、鸡场早已拆除,“冯公窟”的生态环境逐渐好转,迎接我们的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:草木繁茂,池水清澈,鱼欢鸟唱。客人们一边欣赏着“冯公窟”的美景,一边饶有兴味地聆听我介绍“冯公窟”的前世今生,纷纷交口称赞,嘱咐我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“冯公窟”,一定要将这自然美景留给子孙后代!
我感谢嘉宾们对“冯公窟”欣赏和赞美,但“冯公窟”能保得住吗?我对嘉宾们的建议未置可否。自由观赏之时,我独自走上到旁边的一个小沙丘,静静地凝望着“冯公窟”的一泓清水,恍惚间,池面倒映出“冯公”微笑的面容,我顿时似领神意:世无常事,有心即好!
2025年7月16日